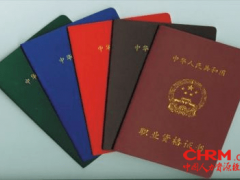HP一事终于闹过去了,即便是众多财经媒体们不甘寂寞、不肯罢休,还想在HP身上捞点注意力,我想也几乎找不出什么可以爆料的点了,再嚼只不过是想体会一下什么叫“索然无味”罢了。
前段时间,看过很多报道、评论HP的文章,多数指出了卡莉上台以后HP积弊的各种战略失误,无论是并购康柏的非成功性,还是放缓invent脚步的惰性,还是单纯依靠小小的打印部门的暴利艰难地原地打转的讽刺性。从这个层面上讲,HP无疑是存在众多战略缺失的。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HP与IBM相提并论,但显然IBM和HP各自拥有不同的命运。IBM自诞生起,幸运地拥有了一代代商界传奇巨子,使得IBM的领导高度、战略高度可以做到高瞻远瞩,可以在窘境中起死回生,可以阶段性地反复成为IT业不同领域的推动者。
相比IBM,HP的运气则糟糕得多,作为卡莉来讲,她既是作俑者、也是牺牲品。她主演的并购戏没有象IBM一代代伟人导演的并购那样精彩绝伦,相反,正因为这一幼稚的举动,为HP的进一步衰败埋下伏笔。
仔细想来,企业的并购无外乎以下几种目的:规模扩张、市场扩张、战略转型。作为HP并购康柏来说,两家企业的重合度较高,所以绝非战略转型;至于规模及市场扩张说,却又忽视了两家企业的渠道本身就存在过高的重合度,并购后不但产生不了1+1>2的效果,最多也就是1+1>1.1而已,结果最后只不过是又给其光鲜的打印部门加了一个包袱,随着PC空间的紧缩,这种压迫感越发明显。
时间证明了一切,等美丽的卡莉明白了这是个战略失误的时候,一定在内心悔恨过自己预见力的低下(当然公开场合绝对不会承认)。此时再回头看看IBM,已然是望尘莫及。10年的时间对IBM来说已经足够喘息,不同的是IBM已经从10年前的现代PC之父进化为了未来几十年的IT服务之王。从战略进化论上讲,HP的战略已经与IBM非同一个段位,做个比喻的话,那就是——奴隶时代的HP和帝国时代的IBM.
再看看HP的执行力。前段时间,孙振耀在接受某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到:“卡莉的离开,并非是对HP原有战略的否定。”这话听起来更象是孙振耀为稳定军心所做的内外公关,现在想来,这绝对是90%以上的套话。卡莉的被“踢”,至少50%是因为战略缺失,而另50%则绝对是其执行力的欠缺。
没有人否认卡莉是个“老美女”,也没有人否认过卡莉是个“强权政治家”。
她可以在各国首脑、要员面前轻易施展美人计,以其浓郁的荷尔蒙气息征服各国政府要员以达到政府公关的目的;也可以以其强硬的手腕遏止内部与其不和谐的声音。曾有HP的员工与我聊起卡莉,称其每天早上都能收到一封来自卡莉的问候信,并因此对其念念不忘。如此容易公关的员工毕竟属于少数,可以忽略不计,一封mail并不能改变其独断独行的事实,这一点,我想HP的董事会体会最深。
Show得固然精彩、荷尔蒙气息再迷人,也只能做个花瓶式的公关总监(业界别名:形象大使)。作为CEO,必须要有强悍的执行力,要让人们看到数字上的变化。而如今的HP,渠道运营成本日益膨胀、流程管理“智障”、品牌自然性贬值,这能称之为执行力吗?另一方面,对于分拆,外部的猜测可以理解,但其内部也是各种思潮涌动、传闻不断,有人称之为“机械式反应”,也有人称之为粗糙的逻辑,还有人说是历史的必然,一切似乎并没有因为新CEO的上台而平息,反而这种胶着在不断持续,陷入一种精神错乱的循环。
“我们需要先强化执行,如果业绩还没有改观,我们再回头考虑战略问题吧。”
HP究竟需要什么?果敢?武断?自负?犹豫?稳重?
这无疑是一个悖论。因为果敢并不意味着武断,犹豫也并不代表稳重,这是一个“度”的问题,而对于“度”的把握正是“执行力”的问题,“度”决定有无,“细节”决定成败。
提到愿景,想起前不久与某财经门户CEO聊过的一段话。
“如果非要找出IT领域的可口可乐,我想也只有IBM受得起这个荣耀。因为IBM不单代表着品质、人性、创新(表层品牌价值),更代表着典型的美式爱国主义实业兴国的伟大抱负(内涵品牌价值),因此IBM给人的感觉是诚信、责任、被关怀。(例证:IBM实业兴国的抱负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IBM规定接受美国军方的订单利润不得超过1%,等等。)”
“IBM一直将自己定位于行业‘推动者’的角色,即便在它最强大的历史时期,也从未以一种‘垄断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而这一切,HP做的到吗?
想起HP在台湾懦弱的PR表演(及广告),再看看其企业管理方面拙劣的执行力、战略规划的疲软,除了“HP=打印成象”,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它清楚自己的终极愿景吗?它在追求比份额更有高度的东西吗?
一个绝对真实的逻辑:理想引发了追求,追求赢得了认可,利润是这种认可的副产品。
HP,有点理想吧。
 手机版|
手机版|

 二维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