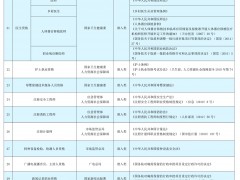在长达20年的忍耐与沉默之后,三位1980年代初就来到深圳的普通劳动者面临着最后的选择:是像其他三十多位同事那样默默忍受命运的不公,还是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被贴上“催搬通知”的员工宿舍 冉小林/图

上世纪80年代初基建工程兵在深圳的“家” 资料图片
最后一战
2007年5月25日中午,刚刚下班的深圳八佰伴中浩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佰伴)的老员工黄有品、申庆东和姜永康接到口头通知:从今天下午开始,不必来公司上班了。
再过几个月,49岁的黄有品、47岁的申庆东和48岁的姜永康就在这个公司工作满20周年了。一个月前,三位老员工向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申请:要求公司按照劳动法规定,跟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当年跟他们一起调到公司的三十多名年轻力壮的同事,现在只剩下了四个人。由于在此前的十多年里,公司都是与他们签订一年期合同,被“炒”的同事只能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黯然离开。
在目睹了三十多位同事沉默而悲凉的命运后,同样的命运也即将降临到八佰伴最后的四位“创业元老”头上,“因为公司要搬到东莞,到时肯定不会再跟我们续约了。”姜永康告诉记者。
这一次,他们选择了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劳动权利。“本来是四个人都提了申请,但有一个被公司一吓,又退回去了。” 姜永康说。
就在仲裁委正式接受申请的当天,公司通知三人“不必来上班了”。此时距他们的劳动合同到期还有6天。
尽管清楚地知道,即使胜诉八佰伴也不会让他们继续干下去,但三位老员工并不后悔打这场“官司”,“我们就是想通过法律证明,我们有这个权利……”申庆东这样说道。
在包括记者在内的许多人眼里,三人所试图争取的“权利”,令人寒碜:不到1000元的工资、长期的超时加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以及名目繁多的罚款与处罚。
“因为公司是制造外销肉制品的,所以车间一年四季都控制在4~8℃的低温中。我们上班都要穿着保暖工作衣,干的全是重体力活。”姜永康说,由于每天在“寒冬”和“炎夏”里来回折腾,他们的身体几年就垮了。公司里新招的基层员工,很少有做满三个月的,“很多人做几天就走了,连工资也不要。”
但就是这份连体力强壮的年轻人也望而生畏的工作,却成了三个中年人以及他们家庭最后的希望。“老公已经干了20年,只想安安稳稳地再干几年就退休了,现在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黄有品的妻子罗云仙说。
曾经也是这家公司员工的罗云仙,四年前被公司“炒”了。因为担心影响还在公司工作的丈夫,罗云仙连劳动补偿都没敢申请,过去四年中就靠断断续续的打零工帮补一点家用。
三个人的家庭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妻子都长期失业,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就依靠丈夫不到千元的工资收入;黄有品和姜永康的女儿正分别上高二和大专,生活费及学费是一笔沉重的开支。黄有品的女儿罗冰冰(化名)为了少花公交车费,每天尽量多走几站路,甚至干脆步行上学;姜永康的女儿姜岚?穴化名?雪在深圳上大专,在学校里每顿餐费从未超过五元。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获得深圳户籍的三位劳动者眼里,这个令无数人羡慕的户口却成了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令在深圳生活艰辛的他们失去了“回家”的权利——没田没地的他们,回去也只能“寄人篱下”。
过去20年辛勤的工作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积蓄:黄有品家的存款还勉强够支付女儿下学期的学费;姜永康则已经在四处筹借女儿下学期的上万元学费了。
就在宣布“不用上班”的当天,公司通知他们在十天之内搬出公司的宿舍,“否则后果自负”,三个家庭至此陷入了真正的绝境——除公司宿舍外,他们在深圳无房可住。
“(不搬)还能有什么后果?”当南方周末记者7月19日来到尚未搬离宿舍的三个家庭中时,罗云仙倔强地说道,“跟搬出去睡大街相比,我们还能有什么‘后果’?”就在20天前,公司派人在三家人住的各自宿舍门旁贴上了“再次催速搬离宿舍通知”。通知中写道,公司将“从劳动合同终止之日起按市价收取房租和水电等相关费用”。
说这句话时,罗云仙的女儿罗冰冰坐在床边有些好奇地看着记者——在过去十多年里,三口之家就在这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生活着:夫妻俩睡架子床的下层,女儿睡上层——“隐私”对于这个家庭是个太奢侈的概念。
在他们的隔壁,一模一样的宿舍里住着申庆东、姜永康和另外那位老员工一家。“那家情况更惨,两个小孩在读书。”私底下,三家人的妻子带着同情告诉记者。
但是在公开场合,三家人跟对方已经不说话,不来往了——怕说错什么被公司抓住把柄。“好像对待叛徒一样。”一位老员工的妻子开玩笑式地这样告诉记者。
“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呢?”唐山籍的申庆东叹着气问自己。在申庆东的记忆里,二十多年前他来到深圳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他一遍遍地向记者讲述当年自己穿着军装“雄赳赳气昂昂”来到深圳时的光荣场景。
命运与尊严
1983年9月15日,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19团的黄有品、姜永康和申庆东以及2万名战友一起,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脱下军装,成为深圳市建筑企业的一员。三人一起被分配到了市建三公司从事基建工程工作。
申庆东至今还记得,自己参与了深圳污水处理厂、远东机械厂、先科大厦等一系列工程,“包括当时的市政府和我们公司的这片厂区,都是基建工程兵建的”。
在那个百业待兴的时期,需要工程兵的远不止城市建设。1987年后,三人先后调入国有企业——中厨集团旗下的华利食品厂,“当时的厂长是个军人,就觉得我们工程兵忠诚勤奋好用。”申庆东这样说道。
当时的食品厂不但工资比在建筑公司高,而且还可以在室内工作,这已经足以让整天在烈日下从事体力工作的战士们羡慕不已,在随后几年里,又有三十多名工程兵来到了食品厂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1993年日本八佰伴公司跟华利的母公司中浩集团合资,华利食品厂被划入合资企业。作为当时企业的核心骨干,工程兵们跟其他员工一起被“打包”转给新的企业。
老员工们既不知道合资谈判的详情,也不知道这次转变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姜永康印象最深的是,在合资后,自己的工资上调了一次——从893元调整为900元,此后的15年里,便再也没有增加过一分钱。
而在此时,他们在建筑公司的战友们工资都已经涨到两三千元,同时在深圳市对基建工程兵的统一优惠政策下,大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相比之下,他们这些在食品厂工作的“散兵游勇”们,不但没有涨工资,也错过了分房的机会。
面对这一明显的不公,老员工们无奈之余,惟一的希望就是在食品厂好好干,干到退休,“到时政府就会保障我们的退休生活了。”对他们而言,这也是“深圳户口”惟一的价值。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发现连这一点期待也变得越来越缥缈,“因为跟外来的临时工相比,公司觉得用我们老员工还是太贵。”申庆东说。
申庆东的判断来自他的观察,“深圳户口的老工程兵都跟我们一样,一家人至少要分一间宿舍”,而当那些老工程兵们被以不同的理由辞退或“自动离职”后,公司便可以在同一间宿舍里安排五六个工人住。
据记者在公司宿舍楼内的调查,四名老兵的宿舍确实是整幢公司宿舍楼里硕果仅存的四间“单身公寓”。
就是为了这一丝“优待”,老兵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长期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低温工作环境令黄有品早在2002年就患上了心脏病和高血压,由于担心公司得知病情后找借口辞退自己,49岁的黄有品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在公司里他并不是惟一这样做的,包括申庆东、姜永康在内的许多员工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心血管类疾病,还有一位任冷库管理员的老兵,在被辞退后不到一年就死于心脏病,年仅40岁。
他们曾经怀疑过这类病跟长期低温工作环境有关,但找不到相关的检测机构,“听说广州有一家机构能做,但我们也付不起那个钱。”罗云仙向记者说道。
2006年11月7日,由于一个近乎“莫须有”的理由,身为嫩化班副班长的黄有品当即被公司领导宣布“不用来上班了”。当罗云仙替丈夫到公司索要辞退证明时,公司却又不给。
“他们是希望黄有品自动离职,这样就不用付劳动补偿了。”罗云仙说,几年前黄有品的班长、老兵邹万财就是这样被炒掉的。
现在龙岗开了一家小杂货铺的邹万财向记者证实了这一判断:“哪有什么补偿,拖到合同到期就当你自动离职。”邹是2001年12月离开八佰伴公司的。
老实寡言的黄有品怎么也想不通,2006年11月12日心脏病突发,被送往孙逸仙心血管医院急救。事隔半年多后,记者找到了黄有品的主治医生罗颖,在看完黄的病历后,罗医生立刻想起了当时的情形。“当时他的情况很危险,扩张性心肌病已经到了三级,加上有高血压,问题就更严重了。”据罗医生介绍,这种病的具体起因还不清楚,但病人大多数是因为长期劳累,加上感冒发烧时没有及时治疗所致。
“心脏就像一个皮球,心肌就是球壁。”据该院护理部主任张静介绍,该病是由于心脏长期充血过度,导致心壁肌肉变薄,并失去弹性。“这种病无法根治,三级以上失去劳动力,四级以上只能卧床,到了中后期只能更换心脏。”
得知黄有品的病情后,公司方面口风突转,宣布要他回去上班。当黄有品于2007年1月底回到公司上班时,发现自己已经从嫩化班副班长变成了修肉班的一名普通工人,工资也被从1050元降到了800元——比深圳最低工资保障线还低10元。
这还不算,本打算靠加班来增加少许收入的黄有品发现,即使在厂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自己也失去了加班的“权利”,“人人都被要求加班,除了我。”身体虚弱的黄有品无奈地向记者说道。
表面上恢复了的工作对黄有品变成了一场“消耗战”:当耗光微薄的积蓄,800元的收入无法再支撑家庭开支时,家庭经济崩溃和自己的“出局”只能是惟一的结局。
一退再退之后,罗云仙和黄有品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被迫离开公司只是早晚的事,他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为了尊严和权利,举起法律的武器。
“我们知道,即使打赢官司我们也不可能留在公司了,但我们就是受不了这口气。工作了20年之后,不能被他们像条狗一样地踢出门去。”罗云仙说。
2007年3月5日,黄有品在福田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公益律师张立飞帮助下,率先向深圳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要求八佰伴公司按照公司合同和劳动法规定,补发黄有品病休期间工资,恢复原工作职位并补发被降职期间的工资差额,总共一千余元。
由于黄有品的“前车之鉴”,加上公司即将搬到东莞的传言,其他的老员工也开始担心起日后的命运来,“到了东莞哪还会要我们呀。”姜永康说。
3月15日,申庆东、姜永康、黄有品和另一老员工(中途退出)依照劳动法第二十条规定,向公司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申请。在多次申请被公司驳回后,三人通过法律援助中心再次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判决公司与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黎总:“法律有法律的道理,我们有我们的道理”
5月30日,深圳仲裁委裁决黄有品的仲裁申请胜诉,要求公司补发黄有品病假工资554.69元及被降职期间工资差额546元。
22天后,八佰伴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无需支付”546元工资差额。认为仲裁委的裁决“偏袒违反劳动纪律,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被告”,对公司“极不公平”。
面对这份起诉书,黄有品的公益代理律师张立飞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可思议”。“我们抛开案子的输赢不说,一边是几乎生存不下去的一个家庭,另一边是这么大的一家企业;500块钱可能还不够公司高管的一顿饭钱,却是黄有品家多活半个月的希望,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呢?”
深圳圣天平律师事务所的顾兴初律师最早经朋友讲述而听闻黄有品的遭遇后,一直无偿给黄有品提供法律咨询。但他听到“八佰伴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后,他认为“黄有品的状况如同一只超负荷的骆驼,八佰伴利用诉讼程序再放一根稻草,这只骆驼就可能倒地不起。诚然,黄有品们的遭遇有着更广泛和更深层的原因,但如果八佰伴稍有一点人道和责任感,对正义稍存敬畏和忌惮,遵循起码的劳动关系准则,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事!”
在向记者解释公司起诉的理由时,三位老兵不约而同地提起了一个名字:“黎总”——一位自1993年开始便担任公司总经理的香港人。
在老兵及其家属们口中,这位来自香港的黎总有着不少近乎“传奇”的事迹:他规定在员工每一次犯错时,让员工写下检讨甚至录音录像,作为多年以后“收拾”这些员工的证据——在黄有品的仲裁庭审中,公司提供的证据大多是黄有品在几年前的此类“检讨”。
黎总还会在年终发双薪时让员工写下欠条,以证明双薪中的一部分是员工的“借款”,一旦发生纠纷需进行劳动补偿时,这部分“借款”自然就被用于抵销赔偿。在黄有品提供的资料里,记者见到了公司以“借款”抵销补偿金的“说明”。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名为中外合资企业的食品厂,早在合资之后不久,中方股东中浩集团因债务纠纷而被冻结股权,从而失去了参与公司管理的资格;而在外资方面,公司控股股东日本八佰伴集团于1998年因过度扩张而破产后,这家食品厂随后被转让给香港四洲集团,成为该集团旗下的生产基地之一。
在这一系列股权变换过程中,自八佰伴时代便执掌食品厂管理大权的“黎总”却凭借着削减成本的“绝技”,安然度过“改朝换代”。而身为资深员工的黄有品等人,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公司“换了主人”。
香港上市的四洲食品2007年中报显示,集团07年度中期营业额与上年同期相近,为2.75亿元,但纯利却增长了66.5%至1687万元,香港股评人士认为,这反映了集团“成本控制”的成果。
黎总所管理的八佰伴,显然是这“成本控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7月24日上午,记者在位于八卦岭的工厂内采访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管理者——公司总经理黎志明。
除了对记者居然会关注“这样的小事”感到吃惊外,黎总不愿意讨论这场争议中的许多具体细节,称“都是下边的人在处理”。
在随后的交谈中,记者明显感觉到,自称“不了解细节”的黎总不仅对许多细节了如指掌,而且常常打断介绍情况的管理人员,对事实进行重新解释和阐述。
当工程部的邹某将劳动争议的原因解释为黄有品在长达一个月时间里“故意省略重要工序”并导致客户退货时,记者忍不住问道,“难道质检部门一个月都没有发现问题?”黎总主动解释,因为质检部门只是抽查,“有可能发现不了问题”。
邹某说,工人与公司的争议,其实是因为公司即将搬迁到东莞,深圳籍的工人担心失去工作。黎总随即打断他的说明,语气坚决地表示,“公司没有搬迁的打算。”
而当记者问及公司为什么要为500元钱的补偿而再次起诉员工时,黎总的情绪激动了起来,“500块钱只是小事情,但是判决事关我们处理事件的程序对错问题。”他显然认为跟500元补偿相比,为公司“正确处理”了黄有品讨个“说法”更为重要。
当记者问及如果法院再度判决公司败诉,公司是否会认错时,这位在谈话中一直宣称公司“完全遵守当地法规”的管理者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如果出现那种结果,只能说法律有法律的道理,我们有我们的道理。”他表示如果一审败诉,公司会按法律程序再度上诉。
事实证明这并非虚言。
7月26日下午该案开庭审理时,自称“从未审过这么小金额”案子的法官当庭要求原告和解,到庭的原告代理人在答应和解条件后,离开审判庭通过手机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请示”,随后回到法庭宣布不接受法庭调解,法官随即宣布原告败诉。
“如果接受调解,他就不能再上诉了。公司之所以明知败诉还是不接受调解,就是为了准备上诉。”庭审结束后,再度免费担任黄有品代理律师的张立飞向记者解释道。
代理过不少此类案件的张立飞指出,“他们就是想把官司拖下去,把黄有品一家拖死!”张律师向记者表示,他曾代理过一个类似的案子,从仲裁到一审、二审,最后拖了近两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即使打赢了官司也是输家。”
就在庭审前一天,三位老兵申请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仲裁也有了结果。申庆东和姜永康胜诉,而黄有品则因为当初华利公司未按规定为他购买社会保险,无法证明自己的工作年限超过25年,因此被判败诉。“我们找了中浩集团,因为怕被要求补交社保,他们不愿意出证明。”罗云仙无奈地向记者说道,即便打赢了官司的老兵们,能否获得规定的赔偿也还是未定之数,因为“公司肯定会上诉”。
在实力强大的公司对手面前,打赢了官司的黄有品及几位老兵,似乎更加悲凉无助。
 手机版|
手机版|

 二维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