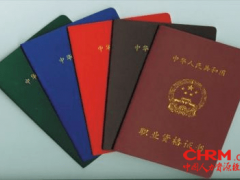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用更好的方式激励年轻人非常重要
经济学正为年轻人提供知识,并塑造了下一代。经济学如何创造、毁灭或塑造未来,以及未来10年、20年将会发生什么?我惊讶于每位资深学者都抱着这么大的热情,思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我们真的应该深入和努力地思考,我们该如何用更好的方式激励我们的年轻人。
但总的来说,这个职业目前情况不正常,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年轻学者可以成功探索的思想空间缩小有关,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疲劳和损耗。我认为至少从历史上看是这样。例如,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发表的宏观经济学论文,当时是所谓理性预期革命出现的时候。最初,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法发表自己的论文,但JPE对他们非常支持。新的期刊创建后,宣扬了这一理论,不管你如何看待这个理论。
我想很多人都承认,这些期刊非常僵化,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持不同政见的记者观点,那些与主流观点不同的观念。重点是,部落主义是存在的,而且不仅仅是在宏观经济学中,实际上在很多领域都有。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我发过几篇论文,当时每个人都对我的问题给出回应。我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宽泛的关于行业发展的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有些不同,但大致上还是支持主要观点。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人们成为第二名和第三名,做收尾工作,或完全不同的工作。比如乔治·阿克尔洛夫,他比较谦虚,但他的论文非同凡响。他的“柠檬市场”论文被所有人拒绝了,后来他终于在一本当时并没有那么权威的期刊上发表了论文。
经济学中的每个重要观点都经历过被拒绝的过程
我注意到几年前,戴尔·莫滕森因搜索理论获奖时,有一本期刊曾多次引用他的论文。这本期刊比五大期刊(比如《国际经济评论》)差很多,被认为是低端出版物。但这本期刊所做的是,选择标新立异的理论,推广这些论文,至少让人们出版新论文,然后有可能获得成功。我们看一些排名,像《国际经济评论》、《劳动经济学期刊》、《国际经济学期刊》和各领域的权威期刊等等并不高,而《世界银行经济评论》,没有人会把它列为前五名,结果成了引文的主要来源。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数据,他们有观点,人们之后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展开论述。
如果有创造力的人得不到出版机会,他们就不会得到关注,但扩展观点、做后续收尾工作的人会得到关注。我承认他们的工作有价值。我不否认,如果有些观点已经流行起来了,那么你就可以跟进和改进。但我要说,关于收尾工作这一点,我认为这应该记录下,在许多领域的每一次浪潮中,我们都要努力找到答案。例如,保罗·克鲁格曼,多年前我看过一些关于他的采访,他介绍说,开始他关于贸易和地理的一些基础研究被拒绝了。不管是哪个期刊,他都不能登上自己的论文,最终他成功发表,他和赫尔普曼合出了一本书。
我敢打赌,经济学中的每个重要观点要得到认可都会经历同样的过程。今天我们听了弗登博格提到的克里克和沃森的DNA报告。但我认为更普遍的是,每一个全新理论都有些怪异。可能你不熟悉这些理论,所以接受不了,因为你不知道如何评估这些观点,感觉风险很高,或者会影响你的同事或你自己立场观点的正确性,那就很危险。
编辑总是关注论文是否符合传统
我有一段亲身经历,我是《政治经济学期刊》的联合主编。这段工作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让我感到困扰。我有论文的推荐人报告。有人说,这篇论文没有新的方法论,所以你不能接受这篇论文。我说:“有什么观点吗?有什么新发现吗?”我会发现论文的观点不是真的错,不是实证的错误,只是与大师们的传统相悖,就像他们以前也不符合传统一样。
所以我发现,作为一名编辑,或者说联合主编,有些人觉得,或者推荐人自己认为,我们必须符合常规。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编辑收到四份推荐人报告,其中三份或四份都拒绝通过,如果你说不,坚持要继续,那么你会被吼,推荐人还会说你无视我们。你要花心思研读这些论文,当推荐人表示不理解的时候,你必须把论文表述得更清楚一些。但尽管如此,对编辑和推荐人来说这依然是很大的负担。
几年前,我是某计量协会的主席。我试图向《计量经济学期刊》提出意见,这本期刊是著名的五大刊之一,我提出的是在线论坛的概念,同时也要进行筛查,因为你不希望有一些怪人发送淫秽内容。但针对对论文发表评论,说“我可以做得更好,再做个技术补充。”其他领域也有这样的先例。开放科学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真正的科学精髓,也是你取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几年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曾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每本书都要经过评审,并必须得到理事会的批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西蒙·库兹涅茨写了一本书,名为《独立职业实践的收入》。他们的理论是,医生收入如此之高的原因是因为成立了工会。这是著名的自由诱饵理论。其中一个人席恩·瑞恩·霍尔,他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理事会成员、《读者文摘》前主管,他写了篇反驳这一观点的论文。他认为也许关于垄断的论点成立,但他们还忽略了另一件事——能力偏见。因为他们只是把医生和非医生人士进行比较,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医生更聪明。早在计量经济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席恩·瑞安·霍尔就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公开参与,人们会说,“这是个想法;我们应该进行审查,然后获得反馈。”
在许多欧洲国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研究评估,都要打出五大刊的记分牌。不是说这个人写的论文有多好,有什么样的观点,而是关乎那个数字。当我们拒绝别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估为什么有人应该获得终身职位。所以我们按照期刊的三星或五星,乘以每个类别的数字就是你的得分,从而避免诉讼和审查。这是个很大的争论,不仅仅是在美国教育中。我们应该允许校长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或者我们应该有客观标准,或者学生标准。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在学生评估方面,许多人认为,更好的政策是对学生进行标准化考核,比如说老师的打分,分数会受到偏见的影响。但事实证明,分数可以更好地预测日后的人生结果,甚至是上大学的成功几率。
虽然其中有风险,但事实是这种情况下的分数,由多名教师打出,去掉最低的5%,最高的5%,得出一个平均值。你可以做一些信息保护,使用这些私人信息时,要以一种经得起推敲的方式,我认为这有些价值,提供了额外信息,所以这不仅仅是偏见。
我们没有研究自己的激励因素
我认为,我们没有研究自己的激励因素,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这是件很值得研究的事情。年轻经济学家面临激励因素以及激励扭曲,如果你有多个目标,你试图实现创造力、生产力,而唯一的奖励是期刊发表论文数量,特别期刊数量。因此,我们要更仔细地阅读自己的论文,并认识到后果是什么。
如果我们还想加强或支持今天发起的活动,我认为可能要有某份权威期刊的特刊,比如《经济文献期刊》,鼓励你与更广泛的人,也许代表不同背景的人认识。我认为这是一种促进开放的方式。然后鼓励更多的实证研究,查看不同的维度,即便在谈论一个项目时,我们也要看到某种革命性想法。克鲁格曼在哪里首次发表了这项研究?发生了什么事?路径是什么?所以看一看宣扬新理论的路径,观察这个行业花了多长时间才承认其中精妙之处,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出格”的全新理论,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有这么多引用次数?
所以我认为把这些记录清楚一些,应用在论文上,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我认为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然后也引入更多人才讨论这个激励问题。经济学中是否存在激励扭曲?这些是如何改变的?这里的一个有趣挑战是,我认为更难解释,我们不能做出什么样的研究?举个例子,有件事不言而喻,即经济史遭受了巨大打击。而经济历史学家通常很难把事情说清楚。他们做这些大型学术研究,任期压力对他们不利,期刊出版次数对他们不利。你不可能写出一份500页的研究报告。
经济学界没有充分利用所有的信息来源
现在很多人都不读书了,所以这方面的激励已经改变了。几年前我和斯隆基金会的人开过会。他们担心,对年轻学者的激励有些扭曲,我不认为他们会坚持下去。我的想法是给那些从事长期项目的学者提供一些激励,继续执行这些项目,至少在研究方面为他们提供资金,也许给他们底薪或让他们在大学里开展研究,但这些激励不能保证10年有效。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但事实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维持当前状态的激励因素是什么,并找出我们遗漏的地方。你可以用一种有建设性的方式来进行评估,那就是看看那些意料之外的问题,还要看所谓证据的性质。如果证据以任何"轶事形式"出现,或者说,“这只是描述性的”,这是很多顶级期刊最忌讳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是。每个人都了解,越来越多人退出这一行业。有种观点认为,这个职业涉及到一系列随机试验。我们想要真正的因果关系。有人采用描述方式。所以亚当·斯密确实是位有自己风格的人类学家,里卡多也有自己的风格。他们在描述现象,使用简单的经济模型和类比来进行描述。我认为这些方式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所以我认为证据的概念需要扩充,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限制。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概念,必须采用统计数据集。
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会议。关于结构性变化的主题。有一群非常优秀的计量经济学家,他们试图查看金融市场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所以他们有非常复杂的工具,所谓的“转换回归”“马尔可夫转换回归”,其中一些是贝叶斯工具。但你看到后会说,“等等,你这里有辅助数据。”那么,我需要一个马尔可夫转换模型来告诉我,1987年或2007年的股市崩盘吗?我们有报纸的报道,我们有新闻报道。我认为这个职业很难去利用所有这些信息来源,包括观察报告。你真的在街上和人对话,你才开始看到现实。
我们的结构没有那种稳定性。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并发明技术来实现的。所以如果你想有人正试图描述中国的技术变化,如果你使用的是20年前的数据集,那就是浪费时间。我们要深入内部,看看技术是什么,谁在实际参与,正在进行什么样的投资。大家认为银行家才去搜集这些轶事证据,这是商学院的人做的事,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会做的。(作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
 手机版|
手机版|

 二维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