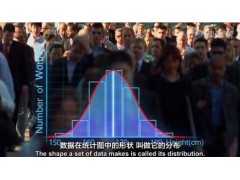绩效往往被认为是现代职场上取人用人的法宝,其实我国古代官场上同样有绩效之说,即阀阅之“阀”。如果说封建时期的阀阅制度使得豪门把持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理应鞭挞,那么现代职场上以“绩效”取人,造成“富二代”“官二代”的骄横同样值得警惕。东汉的思想家王充对世俗以“绩效”取人痛心疾首,他在《论衡》中对的“绩效”的分析值得管理者在选拔人才方面警醒。
不能仅仅以绩效取人
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名列第一,最杰出,也最有影响。他一生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绩效。但是他的志向是致君尧舜,辅佐最高的统治者建千秋功业,因此他对当时以阀阅取人很不以为然。
王充承认绩效的作用,认为是人才都愿意取得绩效。纵横家为例,苏秦和张仪算是另类人物,但是对于他们获得的绩效,儒家不仅不会忽视,而且要引以为楷模。王充认为,司马迁写《史记》时广泛收录卓越人物,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记录成就。因为苏秦和张仪的功绩值得赞美,所以在《史记》中列入了他们的事迹,有意向后代推崇。王充自己在谈到苏秦和张仪时,对他们的功业也非常仰慕:“苏秦约六国为从,强秦不敢窥兵于关外;张仪为横,六国不敢同攻于关内。六国约从,则秦畏而六国强;三秦称横,则秦强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载纪竹帛,虽贤何以加之?”他认为,如果说苏秦和张仪算不上贤人,那么即使当时的贤人得到重用,在业绩上也是很难超过苏秦和张仪的,像稷、契、禹、皋陶等等杰出人物反而相形见绌。
但是,王充认为绩效并不一定与人才的努力成正比,甚至会与人们对健康操行的坚守相背离。这和我们在现代职场上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有的人很努力,但是绩效并不明显;绩效惊人的,其正当性往往值得怀疑。王充指出,有些人“实名俱立,而效有成败;是非之言俱当,功有正邪”,此事古难全。一个人实际努力和名声即使都很不错,但他办事的结果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一个人对是非的评议即使很恰当,但他办事的效果有好的也会有坏的,偶然因素的作用不容低估。王充自己就是如此,他生活的年代正当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对人才征辟举拔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这不能排除王充个人会遭对冷遇。
因此,王充的结论是不能仅仅以绩效取人才,否则对那些没有机会施展抱负的人才极不公平。王充认为,功绩不能用来证明一个人的贤德,就像名声不能用来断定人的实际品德一样。即“功之不可以效贤,犹名之不可实也。”反过来说,一些伪人才倒不难取得绩效:“佞人亦能以权说立功为效。无效,未可为佞也。”如果没有“绩效”,一些伪人才根本就没有市场。因此,有绩效未必不“佞”,无绩效未必不贤。王充还指出,有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创造绩效的机会,如果以绩效评论人才高低的标准,就会将更多的人才排斥在外,直至埋没更优秀的人才。比如在王充年富力强的时候,高层统治者没有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
别让幸偶迷住了眼
绩效与人才真伪的难以对应,与管理者个人的好恶有关。管理者带着个人的思维定势选用人才,不仅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颇为荒唐;而人才的“被发现”就成了一种幸运,他们所创造的“业绩”更多的是借助体制的优势,王充把这叫做幸偶。当幸偶成为一种常态时,难以借助体制资源优势的人才就无法脱颖而出。
王充将人才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够产生治本绩效的儒生;一种是能够产生治标绩效的文吏。如果管理者对人才的选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那么他就乐于使用擅长解决具体问题的文吏,至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圣贤务高,至言难行”,那不是管理者在自己的任职期间的首选。比如当时封建迷信盛行,人人谈鬼。王充希望以理性的方式,去解构民间的鬼传说,破除迷信,颇有科学视野。但封建官僚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问苍生问鬼神,也乐于媚俗,不可能重视王充的意见。反过来说,封建官僚养尊处优,极想摆脱冗杂事务的缠绕,于是就将文吏推到一线处理一些具体事务,以至于“非文吏,忧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选举取常故”。这样一来,像王充这样重视治本绩效、“轨德立化”的儒生类型的人才就被边缘化了。
在官本位体制下,封建官僚的态度对人才的出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部分文吏看中了这一点,不仅媚俗而且媚上,堕落成为“佞人”。他们见风使舵,“人之旧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学术合于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称上。上奢,己丽服;上俭,己不饬。”佞人原来的性格不善辩论,由于君主喜欢辩论,佞人便学着迎合君主饶舌;佞人本来不会作文、由于君主喜欢文章,佞人就会去迎合君主而玩弄词藻。君主奢侈,佞人自己就穿着华丽的服装;君主节俭,佞人自己就不修饰打扮。投机的成功就是一种“遇”,上下的苟合,就形成了体制中的小圈子。王充其实也算是官僚体系的体制中人,但是他从小就不喜欢押昵戏辱等无聊游戏,从来不参与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等儿戏,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进入职场后,他同样不愿意看上司的脸色“权说立功为效”,所以难有知遇之交。
由“幸偶”形成的小圈子可以看作是体制中的体制,层层重叠,由此形成了一种金字塔结构。那么在同一层次的体制中,即使有绩效,圈子内外也会有不同的解读。王充总结为“三害”,即三个层次的伤害:在最低层,竟进者之间为了挣得有限的职位互相低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创新人才的缺点,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这是“一害”;在中间层次,已经获得职位的同僚之间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绩效越来越明显,但是浊吏自渐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绩效反而成为长官重罚的借口,这是“二害”;在小圈子的高层次上,长官被亲幸的佐吏的意见所包围,佐吏人品不高,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心怀不满,必然会在长官面前低毁他。这是“三害”。
力荐体制外的人才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充的思想不乏对“幸偶”式绩效的控诉。这并非控诉绩效本身,而是在控诉其背后的机会不平等。这样的弊端不解除,即使有周全的绩效考核标准也没有积极的意义,“无患斗斛过,所量非其谷;不患无铨衡,所铨非其物”。不怕斗斛不精确,问题在于斗斛所量的是否属于有用的谷物;如果所称的不是该称的东西,手里拿着精确的铨衡也没有用。解决之道就是打破体制壁垒,跳出小圈子的绩效约束。
首先,这需要管理者克服自己的偏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跳出小圈子选人才。管理者在小圈子里听到的往往是附合的声音,那么包容不同意见就成为突破小圈子用人的基础。王充举了一个例子:谶纬之说在两汉之际盛行,光武帝称之为“内学”,他规定不懂谶不得入庙堂之上。而著名学者桓谭对巫师、方士附会儒家经义编造的吉凶隐语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王充认为桓谭是难得的鸿儒大才,称为“素丞相”,与“素王”孔子比肩,将其所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但是桓谭在光武皇帝面前非议谶纬,引得光武帝大怒,要砍桓谭的脑袋。虽然桓谭谢罪叩头直到流血,光武帝还是将其流放。王充认为,假如光武帝能够容忍不同意见,像桓谭这样的人才是完全可以重用的,至少不会贬死途中。
跳出小圈子选人才还需要管理者克己循道,坚持可持续发展。王充认为,封建官僚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启用那些善于“锦上添花”的人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应“以礼防情,以义割欲”,否则虽然可以有一时得计,终将会败露劣迹。所以匡正自己比完善考核别人的业绩更重要。只有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私心,才能产生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动力,那些立志报国的人才才能真正被重视。汉章帝建初初年,中州欠收,王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之后,王充又把厉行节俭具体化,提出“禁酒”的主张。因为时俗嗜酒,而酒是粮食做的,欠收年头禁止人们嗜酒耗费五谷确有必要。但是郡守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不可能真下禁酒令。所以王充只好坐冷板凳,即王充所的说“状留”。
使用小圈子之外的人,要管理者出于公心的力荐,敢于触动体制内的利益格局。在市场经济中,绩效最终要接受市场的洗礼,人才的优胜劣汰在总体上不可逆转。但是在农业经济中,官本位的体制下,对人才的举荐就成为一种“捷径”。这好比农夫装谷子要进城,商人带货要去远方交易,都想创造业绩。如果城门紧闭不能通过,渡口桥梁断绝不能过去,虽然他们有创造良好业绩的实力和愿望,也往往会被排斥在取得业绩的最佳时机之外。所以王充认为,在优秀人才的成长中,需要体制内人的力荐。尤其是对于体制外的优秀人才,一般的推荐很容易遭到体制内的抵制,需要下大力气举荐,而且需要屡次举荐。这又好比世上有棱有角的方正的物体,“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须人动之”;优秀的人才就是世上的“方物”,每动一下,就需要外力助推一次。可见,面对体制内的重重阻力,出于公心的力荐是何等重要。
 手机版|
手机版|

 二维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