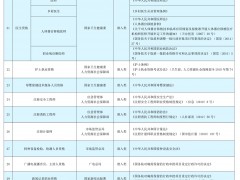我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是一九八二完稿的。寄了一份给戴维德,他读后对一位朋友说:「大家吵了那么多年关于公司究竟是什么,终于给史提芬画上句号。」史提芬者,区区在下也。那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了。几年前遇到一位博士生,他说选修巴赛尔在研究院教的制度经济学,整个学期只讨论一篇文章:《公司的合约本质》。
为了理解「公司」何物,一九六九我开始跑工厂,十三年后才动笔,可见传世之作不容易。然而,整篇文章的破案关键,却来自一九五一我就深知的、当时香港人称为「穿珠仔」的行业。穿者,串也。低贱之极,不见经传,平凡得很,但启发了我。这实例在《公司》文内有提及。
二战后几年,香港西湾河的山头住着些破落户,是贫苦人家,我家一九三八建于该山头,相比起来是「豪宅」了。贫苦人家不少以穿珠仔为生计,一个人从早穿到晚只赚得四口便饭一餐,鱼肉是谈不上的了。很小的不同颜色的玻璃珠子,用线穿起来成为头带或腰带,有点像印第安人的饰物,当时西方有市场。由代理人提供珠子、线与颜色图案的设计,操作者坐在自己家里按图穿呀穿的。以每件成品算工资,是件工。
代理人是老板了。不知是第几层的代理,他的报酬是抽取一个佣金。佣金多少或是秘密,或是胡说,但不同的代理人不少,有竞争,看他们的衣着,整天在山头到处跑——交、收、验货——其收入也是仅足餬口吧。
上述的平凡例子有几个绝不平凡的含意。一、从简单的件工角度看,劳动市场就是产品市场,二者分不开,传统的经济分析是错了的。二、如果政府管制件工的工资,就是管制产品的物价,价管是也。三、没有任何压力团体会对穿珠仔这个行业有兴趣——今天设计新劳动法的也没有兴趣——因为作为代理的老板,作出的只是时间投资,赚取的只是一点知识的钱,身无长物,没有什么租值可以让外人动手动脚的。四、这些可怜的代理老板,就是经济学吵得热闹的principal-agent这个话题的主角人物。这题材可不是起自那一九八三的《公司》文章,而是起自我一九六九发表的《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无心插柳,但八十年代ZviGriliches对我这样说,后来SherwinRosen对阮志华也这样说。至于《选择》一文也触发了博弈理论在经济学死灰复燃,对我来说,是悲剧。
转谈衬衫的制造吧。整件衬衫,从裁剪到不同部分的车造甚至到上钮,都可以每部分用件工算,也往往用。应选用哪种合约过后再说,这里有些问题比穿珠仔来得复杂,从而导致操作的要从住家转到工厂去。在家中操作是有好处的:节省厂房租金与交通时间、可以兼顾孩子与作家务,多多少少有点天伦之乐。但把工人集中在工厂操作,管治与合作配搭的费用较低。原料的处理,在家中可能有困难。当年我调查过一间织藤工厂,藤织品以件工算,但藤枝太长,在家中不能存放。最重要的促成工厂的原因,是机械的设置了。资金的需要是个问题(当年的西湾河不少人家自置衣车,在家中件工操作);工厂可以分两更或三更操作,减少了机械的空置时间;最重要可能是机械太大,家中放不下。二百年前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起于纺织技术有了两项重要的发明,纺织机变得庞大,工厂于是纷纷兴起了。
工厂的兴起,也有几个不平凡的含意。一、工人往往要离乡别井,一百年前中国的旧礼教家庭因而开始瓦解,而今天到处跑的民工以千万计,新春大雪火车站踏死人。二、自甘为奴(见前文)的劳工集中在一起,不仅增加了奴役的形象,加上知识不足,容易被煽动,上街或罢工的行为是远为容易产生了。三、与新劳动法最有关连的,是置了厂房及机械设备的资方或老板,投资下了注,不容易随时无损退出。这其中含意着的租值是一种特别的成本,是不浅的学问,读者要参阅拙作《供应的行为》的第三章第四节——《上头成本与租值摊分》——来理解。这租值的存在可使外人认为劳动法例有可乘之机,可把租值再分配。然而,有胆投资设厂的不蠢,总会想出些应对方法。这些方法一般提升交易费用,导致租值消散,劳方能得甜头的机会甚微,整体及长远一点看,劳苦大众是会受损的。这是因为租值消散他们要分担。
可能最有趣的含意,是新劳动法的推出,如果严厉执行,会导致机械或科技投资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设置了机械的不会再投资,让机械老化,而还未入局的当然会却步了。另一方面,一些厂家会赌一手,多置机械或提升科技,精简员工人数,希望能选中杰出的,被迫提升薪酬可以赚回来。这两方面,皆会削弱劳苦大众自力更生的机会。比较难逃一劫的是有值钱的发明专利或名牌商标的机构。租值明显存在,他们主要的自卫方法是精简员工,减少产出,提升价格。
回头说件工,不是所有产品或产品的每部分都宜于用件工处理的。按产出的件数算工资,工人的意向是斗快。质量当然要检查,但所谓慢工出细活,档次要求极高的产品,检查的费用(包括与员工争议的费用)可能过高了。此外,过于琐碎的工作(例如文员),或有创作性的(例如设计),或不容易界定件数的(例如维修),或需要几个人一起做的(例如电镀),等等,件工皆不容易引进。这里又有几个不平凡的含意。一、选择件工是为了减低监管费用,不选件工是为了减低件数界定与检查费用。都是交易费用,劳动合约的选择主要是为了减低这些费用。二、如果资方投资机械设备,这设备的成本愈高,产出效率较高的员工,愈要有较高的每件工资才能找到均衡点(见拙作《制度的选择》第四章第六节)。这解释了为什么件工制度往往加上奖金制。三、如果件工合约的交易费用过高,时间工资(日工或月工)或其它劳动合约会被采用。但员工的时间本身对老板不值钱,所以监管「奴役」的情况会出现。任何行业,如果有件工与时工的并存,懂得做厂的人会互相印证,务求二者的工资大致吻合。政府干预一种合约,会误导另一种需要的讯息。四、上文提及,管制件工的工资等于管制产品的市价。这里的含意,是管制时间工资其实是间接的产品价格管制。五、如果政府规定的最低时间工资够高,工人会反对件工合约,因为产出斗快其收入也达不到最低时间工资的水平。这样,政府会被迫而废除件工合约。比史德拉、佛利民等大师想深了一层:他们认为最低工资的不良效果是损害了生产力低的就业机会,我补加最低工资会左右了重要的合约选择,从而增加了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上述的五个含意,新劳动合同法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屈指一算,我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合约有四十三年的日子了。主要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合约问题。说过好几次,分工专业产出,获利极大。自由的合约选择是减低交易费用的重点。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交易费用一般高得很。一九八一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我指出,只要这些费用在国民收入的比重略减,经济增长会急升。
想当年,北京的朋友接受了我提出的关于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也同意要尽可能减低这些费用。够浅白,而当时盛行的走后门,交易费用奇高,所以提出的说服力强。跟着的经改有大成是人类奇迹。为什么最近推出的新劳动法,突然间背道而驰,把交易费用大手地推上去呢?是的,从这角度看,新劳动法是明显地走回头路,清楚得很。是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啊,难道这经改要止于二十九年吗?
 手机版|
手机版|

 二维码|
二维码|